甜蜜 温柔 以及隐入尘埃的风花雪月
——读李寂如的长篇小说《十二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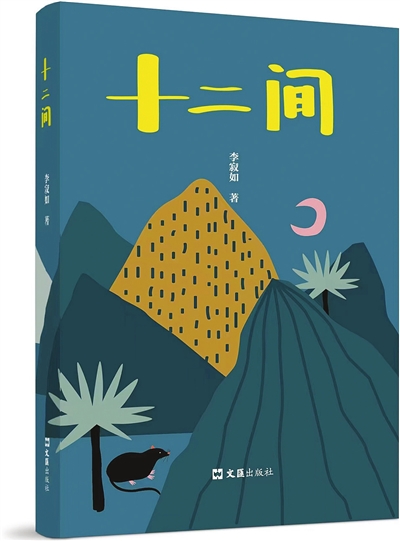 |
徐俊民
春节前的某一天,我在参加了一个活动之后,与同行的朋友来到了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子。那天,天气阴沉,北风呼啸。刚一进村,天空便下起了雪霰子,沙沙地响,接着便是如柳絮般飞舞的雪花,漫山遍野,整个村子一片迷蒙。
忽然有人说了一句:“一进桃花寺,恰有风雪相迎。”“桃花寺?”为了印证我没有听错,便又追问,“你说这里是桃花寺?”
我完全不知道,我那天参加活动之后,会来桃花寺。我之前没有来过桃花寺,却在很早之前听说过这个地方。那应该是李寂如早些年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桃花寺》,故事早已模糊,这个名字却印象深刻。
现在,当我读完李寂如的近作长篇小说《十二间》后,我再一次被那个镶嵌在群山之中清高孤傲的桃花寺给迷住了。
我在李寂如的文字里想起了那天的雪霰子和雪花,我仿佛看见小说里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在用剪子努力地敲打着大块的冰糖,那漫天飞舞的雪花就是冰糖敲碎之后落下的细碎,如同这被风吹散的人间尘埃。
一
李寂如在小说的题记中说,作品是“献给那片有冰糖味星星和水蜜桃香气的土地”的。那一片“有冰糖味星星和水蜜桃香气的土地”叫桃花寺,甜香而温柔,是作者刻意描写的美好之地,同时也为这部小说奠定了感情基调。
小说中那个叫桃花寺的地方,原始、自然、美好。那里的女人丰满、温柔、美丽,那里的男人坚韧、担当、智慧。在那里,人和人之间坦诚、真挚、和谐。而在桃花寺之外,城市邪恶、肮脏、虚伪,那个在桃花寺上进阳光的小学老师杨又侠,离开了桃花寺便被欲望吞噬,失了本性。桃花寺是李寂如着力塑造的故乡,是一个没有被物欲污染的纯净之地。
读《十二间》,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沈从文的《边城》,那个川湘边界上的茶峒小镇,那个充满爱与美的地方,那是沈从文的故乡,更是沈从文的精神归宿地。在《边城》中,沈从文“要表现一种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表现形式’”。在那座“边城”里,沈从文说他“建造一座小庙,在这座庙里,我供奉的,是人性”。
文学作品无法脱离作者的生活经历,经历是作品最好的素材。郁达夫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述传。”那么《边城》是沈从文的“自述传”,《十二间》就是李寂如的“自述传”。这个“自述” 当然不是现实的客观陈述,它应该是一种“精神”的自述,在这一片原始自然美好的香甜之地,李寂如在讲述他对人性的思考。
二
小说以《十二间》命名,说的是桃花寺小学一共有十二间教师宿舍。在新分配到桃花寺小学任教的程小峰到来之前,这十二间宿舍只有一个叫程德寿的老师居住,而之前来学校任教的老师都因为据说在这十二间宿舍中闹鬼而不敢住在学校。
故事其实就是围绕“十二间”闹鬼的事展开。在“闹鬼”的背后交织着桃花寺中的爱恨情仇,故事在层层推进中,抽丝剥茧,揭开了在隐秘的尘埃下深藏着的一段风花雪月的往事。
小说好看,离不开情节的精心设计。对于一个挑剔的读者,常常会根据眼前的情节去推测后面的情节,如果由眼前的情节推测出后面的情节发展,便会觉得索然无味,再阅读下去的兴趣大减,甚至放弃阅读。而《十二间》的情节设计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作者似乎看到了读者心里的想法,让你完全无法通过眼前的情节去推断出后面的故事走向。
小说开头交代了新任小学教师程小峰主动去桃花寺小学任教的原因是听说桃花寺小学有十二间宿舍,他去之后就可以随意选择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对于从小和两个弟弟挤在一张床上的程小峰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而当他如愿以偿地来到桃花寺小学,在除本校程德寿老师之外的十一间房间中选定了八号房间后,情节通常会朝着程小峰如何坚守山村小学勤勉任教的方向发展。然而,故事并非如此发展,一个叫外号“丝瓜”的民办老师为了要把自己的侄女做媒,便装鬼捉弄程小峰,以期他离开“十二间”,住到他家里,好再撮合成就一段姻缘。如果故事按此发展,那么也许可以写成山村教师坚守山村成就一段姻缘的故事,那么便会变得普通而又平庸了。
故而,情节在此一转,由程小峰留下作业做得比别人慢一拍的程小牛而引出程老枪的故事,再由程老枪引出“十二间”白狐的传说,又由白狐的传说引出程德寿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情节总是在你不经意间反转,像翻一座座山,不停地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总是在路上。
小说以程德寿挚爱的女人丁小艺因为小产大出血而昏迷不醒,多年前离家出走的徐小汉将当年他的父亲留给他的“青衣皇后”的角拿出来磨成水给她喂下作结。
这似乎是一个未完成的结尾,然而,这正是小说设计的最精妙之处。我们习惯于追求故事的完整性,习惯于一个或完美或悲伤的结局,却很少去考虑任何人事其实都是“未完成”的本质。生活中的故事本身就是难以终结的,所以小说用“未完成性”作结,本身就是最好的完成。
三
小说最难写的是什么?
我一直以为是语言。
语言从来就不是一种形式,语言本身就是内容,本身就是目的。任何文学作品的成功一定归结于语言。真正的好作品,首先是语言的成功。
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没有鲜活的文字,《红楼梦》不可能成为中国小说创作的巅峰。文学作品最考验的是作家的语言功力,或者说作家的语言功力是一部作品的成功的关键。
所以,相较于情节设计,我会更挑剔小说语言。
《十二间》的语言极精致,极优美。读《十二间》,我常常跟随作者的文字在脑中遐想,那一片冰糖味的天空,水蜜桃香气的土地,还有那土地上一个个温暖的形象,那个叫香的女孩,那个叫丁小艺的女人,还有方金珠、李春梅、阿花……她们有着丰满、美丽、温柔的共性。在共性之下,我们看到了香的青涩与娇羞,方金珠的爽朗与率真,李春梅的压抑与宣泄,阿花的贤惠与忠贞,丁小艺的勇敢与救赎。这些水蜜桃一般又充满母性的女性,性格迥异,个性突出,又如此的美好,让人禁不住感叹这水蜜桃一般香气四溢的文字。
美的语言才能刻画出鲜活的人物。不同于众多丰满的女性形象,男性形象中最值得说一说的人物是程德寿。程德寿是桃花寺小学教龄最长的老师,他从二十三岁来到桃花寺小学,就从未离开过这里。程德寿老师胆子小是出了名的,因为“十二间”闹鬼,但凡来桃花寺小学任教的老师都不敢住在学校,许多老师借宿在本地老师或桃花寺村民家中,从而又因缘巧合与本地姑娘成就一段婚姻。如果程小峰也如之前来桃花寺任教的老师一样,也许也会是与他们一样的结果。而一个胆子小,怕鬼出名的老师程德寿却一直住在“十二间”,直到程小峰的到来,“十二间”一直是程德寿老师一人独守。
很显然,一个胆小怕鬼的人住在一个闹鬼的房子,要么这个人就是鬼,要么装鬼的人就是这个怕鬼的人。程小峰的到来,拨开了这一不合逻辑的事实,真相也随之浮出水面。
二十多年前,二十三岁的程德寿、二十一岁的丁小艺和十九岁的师范毕业生杨又侠同时来到桃花寺小学任教。三个人在桃花寺相互帮助与扶持,成为程德寿一生最美好的记忆。丁小艺身材姣好,美丽大方,深得程德寿与杨又侠的保护与喜爱。而程德寿性格腼腆,不善表达,他把对丁小艺的爱深藏心底。而杨又侠在桃花寺也从未表达对丁小艺的爱,他阳光帅气聪明能干,两年后通过比赛调到了县城小学任教,并与教委领导的女儿谈恋爱,不久之后调任教研室成为小学语文教研员。成为小学教研员的杨又侠,通过组织全县小学语文教学比赛,并且特意给了桃花寺小学一个名额,让丁小艺从桃花寺来到了县城,并且在县里参加比赛,取得全县第三名的成绩。因为这场比赛,杨又侠制造了与丁小艺独处的机会,美丽善良的丁小艺欣赏杨又侠的才华,在不知其已与他人恋爱的情况下,被杨又侠俘虏。等丁小艺看清道貌岸然的杨又侠后,发现自己已经意外怀孕,丁小艺最后在打完胎回桃花寺的途中发生大出血,永远留在了桃花寺小学。
程德寿一生未婚,他一直默默守着“十二间”旁的一方小小墓地,用一生的陪伴诠释一个男人的痴情与坚守。
四
故事由谁来讲述,这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思考的,因为同样一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去说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趣味和意义。我们通常把叙述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也有人把有限视角再分为内视角与外视角。
一般来说,中短篇小说,常常是一个叙述视角贯穿作品始终,也就是一个故事由一个叙述者一讲到底。而在《十二间》中,故事的叙述者不停转换。
小说开头部分,故事的叙述者是外号叫“小蛋糕”的人,采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运用有限视角中的外视角叙述。所谓的外视角,即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一切不全知,叙述者比所有人知道的还要少,他像是一个对内情毫无所知的人,仅仅在人物的后面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小蛋糕”和程小峰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同学,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由“小蛋糕”与程小峰的交流来叙述像他们一样的师范生毕业后的狂妄、迷茫、追求和失落。因为叙述者无法确切知道故事中人物隐蔽的一切,比如,他们的同届毕业生校花秦同学在毕业之后直接去了省城学校任教,他们无法完全掌握这其中的原因,又觉得这其中太不合理,到底是她出卖了肉体,还是真有贵人相助,他们一概无从知晓,因而,叙述者的“不可知性”使故事变得神秘莫测,而又耐人寻味。
而从程小峰主动要求到桃花寺小学任教开始,故事的叙述者由“小蛋糕”转为程小峰,但故事并非采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他”。从叙述视角上说,“他”也不是全知视角,因为程小峰在故事中只是作为见证者的角色(内视角叙述)。也就是说程小峰作为叙述者在场,故事的发展会更加真实可信。
而且,由于叙述者倾听别人的转述,他可以灵活地改变叙述视角,以突破他本人在见闻方面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在叙述中会不停变换视角。如小说中程小峰与程老枪的对话中,在讲述程老枪与阿花的爱情故事时,由于叙述者程小峰无法在场,叙述视角马上切换为全知视角,让故事变得饱满完整。同样,王小二的凌竹采花、徐老秃的灵棺再现、程德寿与丁小艺的爱情故事,在叙述者无法通过见证呈现故事的时候,全知视角就迅速介入,使故事在叙述中不断呈现不一样的精彩。
多种视角的融合运用,可以有效地发挥优势,避免劣势,让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中呈现多种色彩,这是作者对故事叙述的精致追求,也展示其独特的构思艺术。
五
再好的作品也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不同的读者因为认知、学养、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对同一个作品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这应该是一个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十二间》,我也会读到一些我认为有缺憾的地方。
从人物设计上说,小说塑造的第一个女性形象是香,但香最初出场是在学校和本地老师对新任教师程小峰的两次宴请中,再后来是与她的婶婶去桃花寺小学送包子。从情节上看,香中意这位新老师,而新老师程小峰也对香有好感,读者对于香的故事是有期待的,但后续的情节,香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算不算是一种遗憾呢?
另一个是当所有的情节指向程老枪、程德寿等人是“十二间”闹鬼的策划者时,程德寿说编排闹鬼之事,是为了阻止桃花寺村民的乱砍滥伐现象,保护森林资源。我觉得这个设计有故意拔高之嫌,从逻辑性上看也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个设计甚至削弱了“十二间”闹鬼背后的情感力量。
再者,小说开头部分采用“小蛋糕”的第一人称叙述,与后面程小峰作为线索人物贯穿整部小说来对比,似乎有脱节之感。如果把程小峰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或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让“小蛋糕”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再次出现,故事的连贯会更好一些。
马尔克斯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样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样子。我无意间闯入过的桃花寺,现在想起来,也不是原本的样子,而只是我记住的样子。分明清楚地记住了他们的样子。
桃花寺也不是李寂如见过的桃花寺,那有着“冰糖味的星星”“水蜜桃香气的土地”,只是作者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塑的样子。
因为桃花寺,其实是深藏于内心深处的一座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