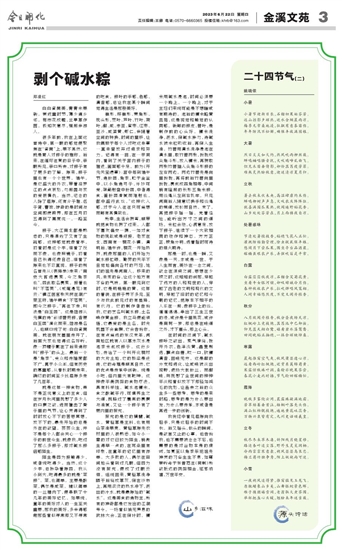剥个碱水粽
郑凌红
白白餈筒美,青青米果新。衰迟重时节,薄少遍乡邻。梅市花成幄,兰亭草作茵。极知欢意尽,强起伴游人。
很多年前,我在上面这首诗中,第一眼的感觉便聚焦在“餈筒”上,果不其然,它就是蜀人对粽子的雅称。后来,在循环往复的日子中,亲眼所见,亲口所尝,对粽子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粽子里也有一个个世界。端午,是它盛大的外衣,带着汨罗江的点点哀愁,勾起国与家的爱恨情仇。当然,纪念的人除了屈原,还有介子推、伍子胥、曹娥,惊奇的是时间与空间即使跨界,却在五月初五得到了高度统一,一路至今。
粽子,大江南北都是熟悉的,只是凑近了又有了生疏感。这种感觉就像看字,初看时是这个字,细看了反而不像。也像照镜子,初看自己长得还像自己,细看了原来也不忍直视。粽子的别名首先从《表异录》走来:“南史大官进裹蒸,今之角黍也”,因此取名裹蒸。接着也叫“不落荚”。《戒庵漫笔》有云:“镇江医官张天民在湖广荣王府,端午赐食‘不落荚’,即今之粽子。”再往下走,叫法是“白玉团”。这是陆游从元稹的诗“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演化而来,陆游是名人,他顺口说了句:白白餈筒美。就在朋友圈里传开了,后面大家也觉得这名好听,像一顶帽子戴在了后来通称叫“粽子”的头上。最后一个是“角黍”,受众和传播度都不广,属于小众派,但有历史的厚重感,从春秋时期走来,确切的时间至少比屈原多走了几百年。
就是这样一种食物,虽不是正统意义上的主食,但在岁月长河里抚慰了多少人的口腹之欲,进而撞击了骨子里的气节,让心灵得到了时时放心不下的苦思冥想。放不下的,最先开始的总是外在的欲望。芸芸众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关心一个粽子的前世今生,就像我,吃过了那么多粽子,却对碱水粽倍感陌生。
陌生是因为接触得少,或者说吃得少。当然,这个少字,总掺杂着原因。我从小到大,吃得最多的就是“菜粽”。菜,也简单。主要是酸菜,偶尔是咸菜。辅以简单的一丝腊肉丁,便串联了十几年的美好记忆。如果说,童年的美好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那我的美好,多半得感谢那些看似寻常却又不寻常的吃食。粽叶的手感、色感、清香感,总让我在某个瞬间觉得生活是那般美好。
锥形、秤锥形、菱角形、枕头形,茭叶、芦叶、竹叶、荷叶,甜、咸、赤豆、蜜枣、红枣、豆沙、咸蛋黄、虾仁,伴随着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星移,让我佩服于每个人对吃这件事一直未曾放弃过追求和努力。记得有一回,在一宗祠内,看到了关于宫内粽子的描述,画面感十足。前为《开元天宝遗事》: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盆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行此戏。”这种代入感,对于今人往往只可遥想而鲜有其情致也。
所幸,生活会拐弯,顺带就把食物也拐了过来。人都不喜欢偏安一隅,一如对食物的挑战或是迎接。老家在北,西南有一桐花小镇。清明后,端午许,桐花一开始热烈,就像那里的人们开始为碱水粽忙碌。勤劳的天平不自觉地偏向各村的巧妇,她们的祖先是闽南人。移来的风,未变的俗,让这个地方有不俗的气质。第一眼见到它时,它是明艳艳的黄。这样的着装,在粽子界不多见,至少与我此前见过的有差异,有代沟。它的制作者告诉我,它的艺名叫碱水粽,土名唤作黄金粽。我立马便能领悟,它最爱的是土名。时光机器不会偷懒,它会告诉你,在有点遥远的东汉末年,闽南地区就有人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包成粽子。这份乡愁,传给了一个叫开化桐村的大片土地,它的桥梁是迁徙,它的命理是顺其自然,它的优点是传承中创新。说是小吃,但内里大有乾坤。这种像平衡阴阳的食物疗法,具有科学性。碱水泡糯米,食之酸碱平行,可谓养生之大道,既躲过了庸常的裹腹与油腻,又让一个粽子有了更内里的探究。
探究的是它的精髓,碱水。黄稻草是主料,也有用山茶油果壳。黄稻草原先农村里的人很熟悉,如今小一辈的对它已较为陌生,稍微生得早一点的,在耳朵里有印象,在童年的记忆里有存单。大多数的人,偶尔在田间地头看到过几眼,但因为没有探究,便成了过眼云烟。话说回来,黄稻草洗净晒干后烧成草灰,倒在纱布上,再用滚烫的热水冲下,沥出的汁水,就是最原始的“碱水”。这是美食的造物主,所有的神奇都是它发出的江湖号令。一场看似悄无声息的武林大会,正在倒计时。糯米用碱水浸泡,时间必须要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对于主妇们来说可能是不想睡或有期待的。泡后的糯米略黄且黏,这是视觉和触觉的认同感。新鲜的粽皮、箬叶,是制作前的心头好。糯米洗净,沥水,倒碱水拌匀,待碱水被米粒吸收后,再倒入生油。竹箬用清水洗净浸泡在清水里,取竹箬两张,折拢成尖角斗形,放入糯米,再捞取两张竹箬插入尖角斗形粽的左右两边。两边竹箬先是向里折拢,再将前后竹箬向里折拢,裹包成四角相等,中间稍有隆起的长形五角米粽,用线绳从左到右扎牢。只见闽南后人随意切换手和线绳的频道,放松而自然。末了,再把粽子摇一摇。凭着经验,能听出方寸之间的道场。米粒会动,心满意足,放下粽子,继续下一个大致相同的动作和神态。方方正正、棱角分明,透着指时可待的烟火期待。
那是一时,也是一瞬,又像是一天,亦或是一世。于人生而言,美妙在一念之间,欲念在须臾之间,思想在少顷之时,这短短的刹那,穿越了远方的人和现世的人,穿越了古老的文明和现代的文明,穿越了旧时的记忆和今朝的记忆,把原本不相干的人系在一起,像粽子上的线,缠缠绵绵,牵出了三生三世的缘,或许是十里桃花,或许是南柯一梦,却总是在味道之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在时间的滋润下,碱水粽呼之欲出。蒸气缭绕,拨开外衣,色泽浅黄,晶莹剔透,蘸点白糖,咬一口,软糯清香、回味无穷。这是甜的分支和进化,让咸味被淡出视野,退场大批粉丝。而甜味,则抚慰了尘世间的种种平淡和看似放不下却轻如鸿毛的忧愁,让品尝之后的众生多一些思考。思考的是来时路,思考的是为什么要出发,为什么要传承,亦或者是再进一步的创新。
我恍惚中看见屈原向我招手,只是这招手的时间不长。后又摇头,低头的瞬间,是欲言又止的心事。他告诉我,他不需要被念念不忘,他需要的是对谷物本身的虔诚,如夏至以角黍祭祀祖先神灵的习俗生生不息,如尊崇听命于东晋范注《祠制》所欲抵达的阴阳相合,驱邪纳福,万世平安。